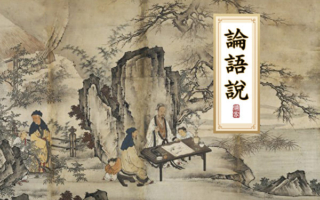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七》)
【注释】
桴:音fú,古代把竹子或者木头编成簰,以当船用,大的叫筏,小的叫桴。
从:动词,旧读去声,跟随。
材:可解做木材。或说同“哉”,古字有时通用。或说与“裁”同,古字借用(朱熹)。
【讨论】
本章颇有名,但解读分歧大。孔子说:吾道是不能行的了。我想乘木筏漂浮到海外去,估算只子路一人会和我同行吧!子路听了大喜。孔子又说,由呀!你真好勇过我,却无所取材。
关于“无所取材”,第一种是诙谐理解,“可惜我们找不到造筏用的材料啊!”《论语注疏》中说:“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戏之耳。”
在此,孔子对子路有所批评。为什么呢?张居正解读:凡人懦弱者,多惮于涉险,子路不以浮海为惧,而以得从为喜,这等好勇岂不胜人乎!然海岂可居之处,孔子岂入海之人,不过伤时之意云尔,而子路遽以为信然,是徒知勇往直行,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宜矣。
钱穆说:此章辞旨深隐,寄慨甚遥。戏笑婉转,极文章之妙趣。两千五百年前圣门师弟子之心胸音貌,如在人耳目前,至情至文,在《论语》中别成一格调,读者当视作一首散文诗玩味之。又说:义理、考据、辞章,得其一,丧其二,不得谓能读书。
第二种,理解为严辞批评,“子路啊我对你无所取用”,“子路没有什么可取的呀”。《论语》中孔子批评子路处甚多,有时还相当激烈。但孔子的教学艺术恰到好处、高明入神,不会总是一副面孔;而从本章文意体会,更应是委婉教导。再联系本章的前后,若理解为严辞批评,则显得突兀。
大家知道,孔子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孔子其实知道吾道不行,但仍周游列国,为什么?因为要在人间留下道。中国行不通,就上海外去,只要有简单的桴,一切危险也都不顾,以道为重。于此,《论语‧子罕》中还有一处记载可相印证——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从这个角度讲,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显得多么英勇豪迈、一往无前、决绝悲壮!可见圣人虽有伤时之意,而终无忘世之心。
不过,有多少弟子能随孔子“乘桴浮于海”呢?可能孔子也不乐观,所以接着说了句“从我者其由与?”这对子路又是多高的肯定和评价啊!
但是,子路虽然勇于为义、临难不避,非常难得,却于“道学问”有不足(《论语‧先进》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因此,本章孔子在激赏子路之余,又指点他“好勇过我”(孔子“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鞭策他提升学问修养。
主要参考资料
《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论语集注》(朱熹,载入《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直解》(张居正,九州出版社)
《论语正义》(清 刘宝楠著)
《论语新解》(钱穆著,三联书店)
《论语译注》(杨伯峻著,中华书局)
《论语今注今译》(毛子水注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论语三百讲》(傅佩荣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论语译注》(金良年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论语本解(修订版)》(孙钦善著,三联书店
《论语今读》(李泽厚著,中华书局,2015)
看更多【《论语》说】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