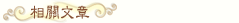【大紀元2025年10月02日訊】許那(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又名許娜,法輪功修煉者,北京獨立畫家、藝術家和詩人。其作品多次入選重要美術展並獲得國家級獎項。因修煉法輪功、參與維權活動、批評時政及揭露中共病毒和防控真相,先後三次被捕入獄,刑期加起來長達十六年。許那的丈夫、與她一同修煉法輪功的知名的音樂人于宙,被捕後僅八天,就在看守所中被虐待致死,至今仍無死亡真相。
許那:生於吉林長春。她成長於藝術家庭的薰陶之中,父親是畫家,母親是東北師範大學藝術系教授。在其自述中回憶,父親經常在家裡畫油畫,松節油與核桃油的氣味瀰漫在兒時的記憶裡,繪畫由此成為她再熟悉不過的表達方式。
一九八七年,許那考入北京廣播學院(中國傳媒大學)文藝編導專業。她並不喜歡這所很多年輕人羨慕的大學,她後來回憶說:「三十多年前,我因政審不合格,不是團員,儘管分數遠遠超過北大的錄取分數線,也被拒收,誤入傳媒大學。」在求學期間遇到八九學運,許那積極參與學運,上街遊行,與同學共同打出「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標語,後來還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靜坐絕食活動。那場被血腥鎮壓的民主運動,為她的生命奠定了自由的底色。
一九九一年大學畢業後,許那對現實失望,拒絕進入淪為中共喉舌的廣電系統工作,轉而進行詩詞創作。她曾以詩人自居,潛心創作出很多詩詞作品,並於一九九三年精選、編撰成詩集《隱蜜》,由灕江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許那將興趣與精力轉入繪畫創作。一九九七年,她的作品《靜物》入選中國油畫學會主辦的「走向新世紀——中國青年油畫展」,並榮獲優秀作品獎。繼而又入選「首屆中國青年百人油畫展」。隨後,許那被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免試錄取為研究生,在繪畫創作上繼續深造。有評論人士指出:「其畫筆法純熟、色彩質樸,有著素人畫家天真爛漫的稚拙和樸素,從畫中能夠感受到藝術家心中的那份美好和平靜。因崇尚歐洲中古時期宗教畫,其作品重視精神性及永恆價值,其作品主題富有詩意。」那些年,許那對世事不聞不問,希望在文學藝術的天地裡像莊子那樣「逍遙遊」,以為可以躲進小樓、歲月靜好。

一九九零年代中期,許那與于宙相戀並結婚。于宙是北京大學法語系高材生,多才多藝,畢業後做了兩年翻譯,後下海經商,又轉而從事音樂創作和演出。一九九八年,于宙加入一支頗受歡迎的民謠樂隊「小娟&山谷裡的居民」。他們的表演屢屢獲獎,後來被業界評為「二零零七年最受歡迎的民謠組合」。
一九九五年,于宙和許那一起修煉法輪功。他們在法輪功中找到了中國社會早已崩壞的群體認同。
文革之後,中國民眾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信仰破滅,陷入信仰危機,於是氣功熱應運而生。法輪功是氣功的一種,且是較晚才出現的流派。一九九二年,退伍軍人李洪志先生在東北創立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是一種結合靜功與動功的健身氣功,同時又包含佛家與道家等傳統思想。一九九零年代中期,法輪功在中國迅速傳播,吸引上千萬人煉功。最初,中共沒有打壓法輪功,且有不少退休高官修煉法輪功,並將其當作強身健體的體育運動來推廣。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光明日報》等媒體發表文章,以文革大批判式的語言攻擊法輪功的經典著作《轉法輪》,法輪功修煉者到北京《光明日報》、天津《青少年博覽》雜誌等多個官方媒體門口反映情況,引起中共當局的警惕,警察抓捕多名法輪功學員。
從一九九六年六月起,法輪功學員長時間接連不斷地給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寫信反映法輪功問題,但是,這些信全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天津發生防暴警察粗暴毆打、非法抓捕四十多名法輪功學員的惡性事件,同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學員不得不到北京國務院信訪辦上訪。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早晨,超過一萬名法輪功學員聚集國家信訪局(距離中南海新華門約兩公里)附近上訪。他們在周圍的人行道上安靜坐著或看書,舉行了持續十六個小時的和平請願。這是自「六四」後十年來中國(中共)政府遭遇到最大規模的和平抗議活動。
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對此表示震怒,要求對法輪功開展鐵腕鎮壓。江澤民在當日晚上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領導人寫信,表示:「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隨後,中共將法輪功定位為邪教,在全國範圍內對法輪功展開大鎮壓和大批判。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法輪功修煉者從全國各地自發到國家信訪局上訪。許那和于宙也來到國家信訪局所在的北京府右街。然而,這一次中共當局早有充分準備,一到那裡,他們就被警察塞進大公共汽車,拉到豐台體育館軟禁。在那裡,她頭一次看到那麼多年輕的學員,大家靜靜坐在那裡,來回走動的是警察和記者。她記得下過一陣小雨,有學員把自己的雨傘給了警察。
後來,被抓的法輪功學員被強制趕進大公共汽車,他們不知道要被押到哪裡去。于宙跑到車頭攔截,揮舞著手臂激動地大喊:「為什麼?不要這樣啊!我們想做好人難道有錯嗎?」但于宙被警察拉開,推進車,與許那一起押送到中關村派出所。在那裡,許那見到滿滿一院子的學員,多數是人民大學的師生。在警察的包圍下,他們被強迫傾聽警方宣讀中共當局對法輪功的定性。
後來,許那在回憶文章《當恐怖侵入日常生活,講真相要付多大代價》中寫道:「當恐怖侵入生活的日常,在一個謊言鋪天蓋地,信息嚴密封鎖的國家,講出真相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多年以後,想起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這個日子,我才意識到,那一天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當然也改變了我們。」
隨後,許那和于宙再次前往天安門抗議。剛剛走出地下通道,他們就被便衣攔住:「你們是煉法輪功的嗎?」他倆異口同聲地回答:「煉!」一個「煉」字剛一出口,他們就被驅進等在旁邊的警車,之後關了一個月。
二零零一年七月,許那為外地來京的法輪功學員提供住宿、散發法輪功相關資料,被北京警方逮捕,隨後被以「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刑法》第三百條)判刑五年。中共通常以《刑法》第三百條來構陷和迫害法輪功及其他宗教人士。流亡美國的人權律師吳紹平表示,中共用《刑法》第三百條來迫害法輪功,是「口袋罪」,是錯用,違反憲法。而且,給法輪功貼邪教標籤,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許那被關押在北京女子監獄。在這所監獄,每天只讓囚犯睡四個小時,白天要幹重體力奴工活。許那進監獄的第一天,就被分配了普通犯人訓練一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一天做六百雙拖鞋的鞋幫子。許那出獄後在題為「法輪功女學員獄中歷練」的自述中寫道:「我多麼希望自己被關押的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而不是中國的監獄。因為在納粹的毒氣室,人可以迅速死亡,而在北京女子監獄,它讓你活著生不如死。反覆經歷漫長的酷刑,酷刑中她們配備懂醫的犯人看護,隨時檢測你的體徵。我在那多日不許睡覺,被發現心律不齊。於是警察命令說:『讓她睡一小時,休息一下。』」
許那還詳細描述了各種各樣隱蔽而精緻的酷刑,比如:劈叉,將雙腿拉開成一百八十度,命令三個犯人坐在雙腿及後背,反覆按壓。警察自豪於這個發明:「這個辦法好,因為疼痛難忍,但又不傷及骨頭。」在獄中,許那承受過十一種不同的酷刑折磨。
北京女子監獄常常給許那調換地方。監警頭子發現,許那有改變別人的能力,讓所有和她相處的人都與之友好相處。二零零二年底,監獄長看到不但不能轉化許那,反而許那影響了很多人,決定把許那關押進小號,加重迫害,使她無法接觸其他囚犯。
許那通過親身經歷指出,中共的邪惡超過了納粹:納粹反人類的目的是消滅猶太人的身體,而中共的目的是摧毀人的精神、良知。當她在酷刑與洗腦中更加挺直腰板時,一個警察認真地對她說:「應該申請對你進行開顱手術,把你的大腦摘掉。」
二零零三年,許那當年的大學同學、央視節目主持人徐滔來採訪北京女子監獄,許那被隔離在警察辦公室。當時的場景比卡夫卡的小說還要荒謬:四個犯人,以人肉拷子的形式鉗住許那,她清晰聽到不遠處採訪現場,曾對她施予酷刑的警察和犯人在宣講如何文明執法,而她不能發出一點聲音,她的嘴裡被堵上了毛巾。那次採訪後不久,法輪功修煉者董翠被活活虐死在女監。監獄當局稱董翠為病死。許那因檢舉、控告董翠被虐死的事實,再次被投入小號折磨。
出獄後,許那發現,她離開了小監獄,卻進入一處大監獄。她感嘆說:「那些自以為自己在中國自由的人,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摘除了精神,生活於一個無形的大監獄中,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你認同它存在,認同它應該繼續存在,獲罪於天,豈能長久?所以每一個被扭緊的螺絲釘都是有罪的,如果它加固了這個機器的邪惡運轉。」

許那和丈夫于宙沒有放棄法輪功信仰。他們積極參與法輪功的活動,傳播有關書籍,屢屢被警察傳喚和騷擾。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晚,許那、于宙夫婦開車回家路上被警方攔住搜查,警察在車中搜出法輪功書籍、神韻及六四的光盤。於是,警方將夫婦二人帶到通州拘留所審查。
八天後,體格健壯的于宙突然被宣告離奇死亡,時年四十二歲。這一天正是中國黃曆的大年三十。警方聲稱,于宙死於絕食或糖尿病。他的遺體蒙著白單,在二十多個警察包圍下,家屬不被允許接近。家人強烈要求解剖遺體,但當局解剖後一直不公布結果。許那要求警方提供丈夫在監室內的監控錄像,警方卻告知:監控已損壞。許那與于宙的父母拒絕簽字火化遺體,于宙的遺體遂長期凍在冰櫃裡。
幾個月後,許那被北京市通州區法院以同樣的「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判刑三年。她在獄中再次經歷了地獄般的折磨。三年後,她刑滿釋放前,被當局警告:「立即火化于宙的遺體,嚴禁再講此事。」
許那沒有放棄探尋丈夫死亡的真相。她常常想起跟丈夫的最後一次長談,他們細數若干死去的法輪功修煉者時,于宙沒有什麼感慨,只是說:「將來我們倆中,不管是誰,如果為講真相、維護大法而死,剩下的那個人,一定不要難受。我們為真理而來,朝聞道、夕可死。」二零一二年,許那與王導演(她的大學同學)合作,祕密拍攝了一部講述丈夫生平經歷的影片《缺席的人》。
許那透露,有一位姓鮑的自稱是于宙所在監所的「牢頭」來找過她。此人告知:北京「十佳」警察董亞生指使他與另外三名犯人就于宙的死因給檢察院作了偽證。但于宙死亡的真相,他仍不肯全部說出來,理由是「我害怕被滅口」。
許那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她這次出獄的感受:「二零一一年出監後我發現,這個表面看起來很難改變的國家,因一張光盤、一張傳單、一個破網軟件,真的發生改變了。」她認識了很多年輕一代的、更加勇敢堅強的法輪功修煉者:「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時,他們還都是五六歲,如今,他們作為新中國人的一代弟子走進修煉並被迫害。當恐怖侵入生活日常,謬誤與偏見主導整個社會,人們很容易屈服於暴力與軟弱,只能意意以求個人幸福、罔顧他人苦難。他們卻有著堅持正義立場的勇氣,他們的故事就是與這個世界的冷漠、自私、功利抗衡的過程。他們所爭取的不過是正常國家人人都會有的權利。他們被迫害,讓世界看清了中共,也又一次提醒國人:我們到底生活在怎樣的國家?在這片土地上,一個動作、一個聚會、一本書、幾張照片,就會招致牢獄,而這一切已持續了二十多年。這一切不能再延續了,因為天理昭昭。我們並非生活於動物的叢林,人類社會不是它肆意橫行的樂園。」
許那也沒有停止藝術創作。二零一二年,她先後在北京西五畫廊舉辦個人作品展及參加北京市與台北的藝術展,她的作品也在香港引起藝術收藏家的關注。
許那的一位後來流亡海外的朋友說,許那在丈夫去世後沒有消沉下去,「她說話很有條理,聲音透著一種篤定。儘管丈夫去世,她仍堅持該做的事情。她很勇敢,很堅韌。」她說,許那經常默默地幫助別人:「她個人有一些積蓄,不太多,如果看到別人有困難,會伸出手去幫人。不太考慮個人的得失。她關心別人,非常細緻,很像一個媽媽。」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許那再次與另外十名法輪功信仰者一起被北京順義區空港派出所警方抓走,住家遭查抄,手機、電腦等電子設備被搜走——那時,他們正在拍攝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間北京的街景和日常生活,並提供給海外的大紀元等法輪功背景的媒體。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許那被北京東城區警方以涉嫌「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轉為刑拘。九月一日,被北京東城區檢察院以同罪名正式批捕。之後,許那等多人的案卷被北京東城區警方移交給東城區檢察院準備起訴,但因東城區檢察院核實後認為該案「證據不足」,兩次退回卷宗要求補偵。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許那的辯護律師梁小軍去看守所會見許那,隨後在推特披露:「以許那為『主犯』的十一人案件已經起訴到東城區法院。因他們特殊身分(法輪功學員)而起訴的罪名,無法掩蓋他們言論自由被限制的事實。」梁小軍對許那很讚賞和敬佩:「殘酷環境之下,她淡泊名利。她本應有的名氣與影響被民間社會所低估,卻為官方所不敢輕視。每次會見她,於我,都是一種聆聽與學習的過程。……這次去會見她,她已經收到了起訴書。她說:我第一次被抓的時候,這次和我同案的這些孩子(那時)才兩三歲。如今,李宗澤等十位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將遭遇判刑,不過僅僅因為他們拍攝了幾張疫情期間北京街頭最常見的真實照片。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將被吊銷律師執照的梁小軍在推特上表示,他趕往看守所會見了許那。這是一次為了告別的會見。梁小軍說,「她關心我,總在問我的情況。」「感恩那些我曾經在看守所會見過、在法庭上為之辯護過的人權捍衛者、民主人士和宗教信仰者。」十一天之後,北京市司法局以「公開發表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為由,吊銷了梁小軍的律師執照。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許那案在北京東城區法院開庭審理。許那等十人已被超期拘押一年半左右。許那第三次被以「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定罪,判刑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並處罰金兩萬元。
許那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八日,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刑。
二零二三年九月下旬,許那被轉到北京女子監獄服刑。家屬多次要求探視,均遭獄方刁難,至今不讓會見。
美國國務院、歐洲聯盟駐華代表團多次呼籲中共當局釋放許那。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CIRF)均將許那列入資料庫,予以特別關注。
許那曾在文章中表示,她不會向中共的極權暴政低頭:
如果你想擁有它所允許給你的「獲得感」「安全感」,你就要學會如何忘恩負義、指鹿為馬、助紂為虐,並為之塗脂抹粉,成為它的一部分,成為假惡暴的一部分。我終於看清它為什麼迫害「真、善、忍」,就因為它是假、惡、暴。作為一個從來不關心政治的人,我終於認識到:必須講出它謊言之下的真實歷史,讓人看清七十年來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誰是一切災難的元凶;必須講出它如何滲透億萬中國人的頭腦,侵蝕國人的心靈,瘋狂其理智、扭曲之人性。
覺悟這些之後,我不再害怕被人說成是「反革命」「反黨搞政治」。面對這種沒有人性的、踐踏天賦人權的政治,如果我沒有明確的態度,如果我不反對,我必是逆天的,我必是軟弱自私的,我必是與邪惡為伍!而反對它才是真正的愛國,真正地為國人的未來負責。
許那還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
多年的親身經歷使我覺醒,這個國家的每一件不公義都離我很近,我不能裝作看不見,它最後真的發生在我的身上;這個世界每一件不公義,即使離你很遠,也與你息息相關,因為他時刻拷問著你的良知。有些事與我不僅是權利,也是責任,我無可逃避。
許那現被關押在北京市女子監獄(編註)
通信位址:北京市大興區天堂河慶豐路滙豐街潤荷巷3號
郵遞區號:102609
聯繫電話:010-53867036
接聽時間:工作日8:30-16:30
本文轉載自余杰著《永不屈服》(《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第三卷),(台灣)主流出版社2025年5月版。
編注:許那於2025年3月間被非法加刑1年半,駁回上訴,送回北京女子監獄單獨關押。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