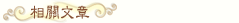來,坐到我身邊。聽我對你講一個故事,關於活著,關於生命和愛,關於靈魂的終極歸宿。這是一個長長的上海故事,來到上海和離開上海的故事。
在煉功點上,我學到了一個新的名詞: 同修。「同修」是指一同修煉大法、在修煉路上攜手前行的同伴。我愉快適應了生活裡有了同修這群人。在我心中,「同修」這個稱呼充滿了神聖與敬意。
身體不再有病痛,我每天忙得精神抖擻,清早與同修們一起煉功,日常照顧家人,有空就學法(讀《轉法輪》)。我的天目又能看到很多神奇的景象了。兒時的記憶,從遙遠的天體往下掉,掉到無底的深淵——再一次復甦在我25歲的夢境裡。不同的是,現在的我是從深淵裡,不斷地往上升。隨著我實踐《轉法輪》做好人的道理,我的天目看到,我的真我,飛過一層又一層的天宇,一層天比一層天更美好——如此不斷地往上升華。我知道了我的真我來自遙遠的天體,而修煉,則是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九九九年五月底,煉功點上不時出現一些陌生人,衣著神色迥異於晨練的人群,他們散布四周,不動聲色,卻聚焦於我們煉功點,還時常舉起相機對著我們拍照。
見此情景,我心頭泛起隱隱不安,但是依然每日清晨前往煉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的上海,淡淡晨霧,陽光穿過晨霧,灑在弄堂裡的青石板上,七月流火,空氣中瀰漫著夏日特有的溽熱,我來到煉功點。只見一大群身穿制服,全副武裝的警察已經守候在煉功點了。他們厲聲地驅趕在場的所有煉功人。為首者對我們宣布:「政府已經取締法輪功了。以後不許聚集,不准到這兒來煉功。」
我的心頭充滿了疑惑不解:這麼好的功法,我煉功短短的日子便受益匪淺,政府為什麼不讓人煉了呢?是不是政府搞錯了?我得去向人民政府反映情況,希望政府改變取締法輪功的錯誤決定。
想到這,我騎上自行車,直奔上海政府信訪辦。到了市政府門口,法輪功學員們正在三三兩兩,匯聚而來,每個人神色凝重。我看到了一位我熟悉的學員,問她:你怎麼也來啦?
她用上海話,對我滔滔不絕,如訴家常:「我煉功前,是癌症患者呀!通過學法煉功,我全身病好啦。現在政府不讓我們煉了,我能不來講講我的親身經歷嗎?」
我環顧四周,周圍這些人和我一樣,身為人民中的一員,來向人民政府反映自己的真實情況。每個人都抱著滿腔真誠,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例證,想來告訴政府這功是好的。
到了中午,政府有人傳話出來,要學員選出幾名代表,向政府反映情況。於是,有幾名學員自告奮勇地從人群中走出來,進到政府大樓裡。
這時,有人提議:「大家不要堵在政府門口堵塞人行道。大家請到廣場上去等待。」
我便隨人群來到人民廣場音樂噴泉四周,當時大概有兩千人左右。炎炎烈日下,有人在一起煉功,有人聚眾小聲在交流,還有人則靜靜看書。
過了好長時間,進政府大樓會談的學員,才走出來。且很快,有警察過來,以查他們每個人的身分證為由,把這幾人全部帶走。
警察把廣場圍成一個圈,第一層是上海各單位的領導被通知到場,勸說本單位的學員離開廣場;第二層則是眾多的警察圍成的包圍圈。外邊的第三層看起來像流氓,有的手臂上還有紋身。包圍圈就緒後,廣場上的局勢陡然緊張,數輛大巴車呼嘯而至,車門打開,一排排警察迅速湧出,驅趕學員離開現場。有單位或有地址的,按照地段依次上大巴,送離廣場。大部分人上了大巴,人群也就散了。還有幾個學員拒絕離開廣場,被警察動手毆打,強行推搡著架上了車。我目睹這一切,想到阿寶並不知道我的去處,他下班回家後要找不到我,會很著急。於是我騎上自行車,自己回家了。
我到家了,打開電視,所有的電視台都在滾動播放詆毀誣陷法輪功的新聞報導。
此時,門外急匆匆走進來阿寶的爸爸,他是看到新聞,就火急火燎騎車趕到我家。他神色緊張,大禍臨頭地對我說:「小夏,你看電視了嗎?趕快別再煉了!」
我難過地說:「爸爸,電視裡都是造謠!你們知道的,我的身體就是因為煉法輪功煉好的。你們親眼看見的,不是嗎?」
公公一時無言以對,臉色一沉,也不曾坐下,復又關門離去。
此時,窗外暮色降臨,夜空裡傳來熟悉的鴿哨,四鄰的廚房裡,聽得見開水龍頭洗菜,熱油爆鍋的家常聲音,孩子們在水門汀上踢球,嬉戲打鬧。看起來一切如常,然而,我的生活,從七月二十一日這一天開始,從此改變了。
第二天,居委會派來兩名婦女,她們敲開我的門,開門見山,嚴肅審問的口氣:「你什麼時候開始煉功的?」
我如實回答:「幾個月,不久之前。」
「家裡還有法輪功的書嗎?書必須上繳的。」
我心裡一陣難過,只搖搖頭,不再說話了。
她們狐疑地打量我一番,問不出來什麼,才離開。
我從弄堂經過,感受到空氣中瀰漫著令人窒息的敵意。弄堂內家家戶戶都在收看誹謗大法的新聞,乘涼的人們的扎堆議論聲,充街溢巷。我們煉功點的同修們,再也無法在一起煉功了。
被大巴車送走的學員,事後對我說起,大巴從政府門口將人拉回住地,不是直接回家,而是停在了居委會門口,由當地居委會詳細登記了每個人的姓名、家庭住址,才可離開——也就是說,登記在冊的法輪功修煉者,自此就被居委會派人監視起來了。
阿寶執意不讓我出門,我只能藉口上街買小菜這個外出機會,趁機尋找失散的同修。有一回,在菜場裡,我遇見了教功給我的李瑋紅,她看起來神情憔悴。想來我在她的對視裡,也是憔悴和憂慮的。我望著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淚水瞬間湧出眼眶,在人來人往的菜攤前,我無法自制地淚流滿面。
李瑋紅走到我面前,輕輕拍拍我的肩膀,一如第一次對我說話時的溫和,道:「我們只有在家多學法。等這一切過去吧。」
點閱 苦海泅渡回歸路 系列文章
責任編輯:李明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