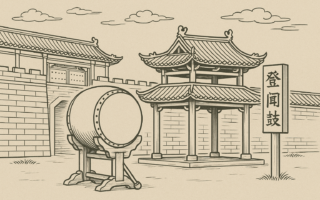【于少保萃忠傳】第二十五回:神僧指水怪形藏 于公存海涵度量

徐有貞當日在庵內,再三叩問老僧。老僧見有貞虔誠,對有貞曰:「大人經綸天地,包括萬理,豈不聞仁者無欲之言乎!」徐公心中頓悟此語,乃曰:「如老師之言,莫非其下有巨魚乎?魚性貪餌,吾以豐餌巨鉤,必能獲也。」老僧曰:「非小可也,非易取也。洪口之下,極其深邃。內有一怪,潛身幽底,似蛟非蛟,似鱷非鱷,形長力大,口能吐波發浪。所以才築得就被他哄坍,非水勢之惡也。皆因此怪在下搜決,因此難築。」
有貞見說甚驚,乃曰:「若有此怪,必用千夫巨餌,方能獲捉。」老僧笑而答曰:「大人雖用萬人,亦難捉取。若必欲以人力勝,惹他性起,連附近人家,皆遭其害。吾今傳大人一法,自然除惡,不損於人。」徐公忙叩問曰:「老師有何妙法?」老僧曰:「大人回去,可急取三五千擔石灰,裝載多船。先令人吩咐往來船隻、附近人家,暫離此數十餘里之外。限五日,不許人行動往來。至日,到於洪口,可擊鑼為號,一聲鑼響,齊把石灰傾下水底,急把快船飛搖放遠,待水底石灰滾化,發蒸起來,此怪必然煮死。除了此怪,那時因水勢而導之,堤必成功。」
徐公蒙僧指示,即叩謝辭轉,急急與眾下山回府。速差人取備石灰,按法行之。果然一夜後,聽得洪口水滾如雷。少頃水高接天,衝倒近處房屋無數。居民預先得了曉諭,暫移無害。至第三日後,有貞見洪口水勢不高,波平浪息,乃令人駕快船數隻,前出哨看。哨船之人果見一怪,身長數丈,遍身鱗甲,頭如豬而有鬚,前有二爪,後有鱗尾,形甚兇惡,浮死於水面之上。哨船人來報有貞。有貞親往觀之,果覺駭異。識者曰:「此豬婆龍也。」
有貞連夜並工修築,又三月,此堤將成,忽然大雨,連堤滿漲,水甚湧溢。有貞又掉船細察其故,製數木鵝放水中,順流而下。又投之以物,使人往數里候看,物與木鵝皆浮出,惟一處木鵝不浮,投之以物皆沉。有貞曰:「此水源也。」忙令人塞之,不止,有貞悶思曰:「向者蒙老僧指示,得除此怪,堤將有成。不料秋雨瀑漲,洪水泛濫,其害終在。吾因思窮其源,今源已知其處,奈塞之不止。」
思量久之,不覺隱几而臥。少刻,見二人立於案前。有貞忙問曰:「汝二人何人也?」二人曰:「我河神也。先年因張湫洪水大泛,民遭漂溺。官司屢督工築堤不就,役夫死者數千。吾二人不忍見眾漂沒,乃對天立誓,願捨身以救萬人。我二人遂跳入洪口,其下果有一怪螭在下,與戰一日夜,被吾二人斬之。水就退,沙就長,而堤成。上帝憐吾二人為眾捨身救患,敕吾二人在此守護洪口。今公水源雖尋著,而其下尚有龍窟珠淵,非石沙與土所能塞之也。」有貞忙問曰:「用何物可塞?」二人曰:「可鑄長鐵柱,與大鍋底貫墜於下,自然塞住。」徐公聞言大喜,問二神何名。二人曰:「吾乃郝回龍、鄭當柱也。」言畢覺來,乃一夢耳。
有貞忙出廳問之,適東平判官王震到廳稟事曰:「卑職蒙差濬河,前日見一石板上書著:「鄭當柱、郝回龍為眾捨生。在水中,幸遇王州判,移我顯聖河東。』卑職不敢隱默,特來呈稟。」有貞聞言,心異其事。遂語以適才得夢之由,王州判曰:「此分明神之顯聖,大人當急為之。」有貞遂依夢中所傳之法,用鐵柱鐵鍋下之,隨用石沙去塞,漸塞漸築,而堤遂成。有貞感二神傳法,乃建祠奉二神於洪口。復上疏開神之功績靈顯,遂名其廟曰「顯惠」。至今往來商賈居民禱祀之。
有貞乃從金堤張湫起,逾百里而至大豬潭。西南行九里至濮陽,又上數十里至范陽,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沚,其水勢隨平。凡河流旁出不順者,築堰堰之。堰有九處,長闊皆萬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從北出,以濟漕渠之淺涸。又於數百里之中置閘,由龍灣於東昌、魏灣,共置八閘。積水過丈,則放泄皆通,流於古河,以入於海。又鑄精銅、精鐵,雜為元金之物象數百斤,以鎮定之,取金水子母之義也,名曰廣濟閘。歷三年,功始完備。有貞共差人四萬五千,分面作長役者一萬三千。用木植大小十餘萬,竹六十餘萬。至今漕運。並商貿船隻,往來稱便。
徐有貞築堤成功之後,尋思往日西山老僧指示之功,乃令人備禮,前往致謝。數日回來,稟覆道:「小人們蒙差遣,仍用尋蹤到庵。只見松崖翠壁依然,金亭玉柱如舊。其庵空,其者僧與白尾騾,不知所往。但見石庵柱上,高題一偈,寫著留與治水徐公。因此小人們錄此偈呈覽。」其偈云:
指示汝成堤,從此賴無虞。
日前多朗照,後漸進彌迷。
越五重華曜,於忠實爾為。
南金當有遇,歸莫檢篇遺。
有貞看畢,不解偈中之意。乃曰:「此真神僧點化,吾得除水怪以成堤功。恨吾歸心太急,不曾參問得禪機。若再相懇,必有教益。可惜無緣。」嗟歎一回,留月餘,乃治裝還朝。朝廷因有貞治水有功,升禮部侍郎,加僉都御史,支二俸住京。其年京師大旱,有貞薦唐段民能祈雨。段民應詔,果祈下甘霖尺餘,不致饑歉。不多月,段民得病身故。朝廷遂蔭一子入監。
有貞在京一年,因國子監缺祭酒,復浼于公保薦,于公即使保奏。過數日,于公奏事於文華殿。景帝獨宣于公至面前,曰:「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心術機險,豈堪為祭酒耶?若用之,豈不壞了後生輩也?」公見諭,惟叩謝辭出。左右見景泰召公當面,遙聞有貞祭酒之旨,傳與有貞。有貞只道于公不薦他,又在上前說他過失,甚恨于公。兩次不如所願,遂爾成仇不解。冤禍於此基矣。
于公平日只知輔君匡國,練兵養民。惟直道而行,於心無愧,不知旁忌匿怨者多時。有兵部侍郎王偉,原任職方司郎中,于公見偉有才思,遂保舉為本部侍郎,鎮守大同諸處。前者于公遺計於偉,致小田兒(賊名)之死。遂召回同理部事。未幾,于公以多事匆忙,偶然詿誤一事。王偉遂密奏於帝。
一日,景泰召公於便殿,以偉劾疏面授于公。公叩頭認罪。帝慰諭曰:「朕自知卿,卿勿為慮。」于公蒙景泰授王偉之疏,感恩叩謝而出。
王偉見于公回部,忙出迎曰:「今日有何聖諭?何事商確回遲?」公曰:「姑進內言之。」既到堂,偉又曰:「聖上何事議論?」于公笑曰:「老夫政事冗繁,稍有不是之處,賢弟當面言之,不佞必然相從,何忍為此。」隨出袖中所劾之疏與之。王偉跼蹴無地。公復慰曰:「不佞素無夙憾。自今之後,有不到處,煩賢弟面教,足見雅情,不必介懷。且國家多事之秋,部事非一人可理。得弟輔成,足沾厚意。」王偉此後愈加恭敬于公,公亦厚待王偉,無纖毫芥帶於心。有事彼此商議,然後施行。
公一日與偉商確兵政,忽有人報道:「廣西總兵武毅上本劾奏思明州士官黃![]() 弒兄大變事。」公正欲問時,早有武毅揭帖呈上。于公看畢,查訪其事。不數日,人報道廣西思明州土官黃
弒兄大變事。」公正欲問時,早有武毅揭帖呈上。于公看畢,查訪其事。不數日,人報道廣西思明州土官黃![]() 有本奏上。朝廷旨下,著眾官會議。未知所議何事。
有本奏上。朝廷旨下,著眾官會議。未知所議何事。
(點閱【于少保萃忠傳】系列文章。)
責任編輯:李梅